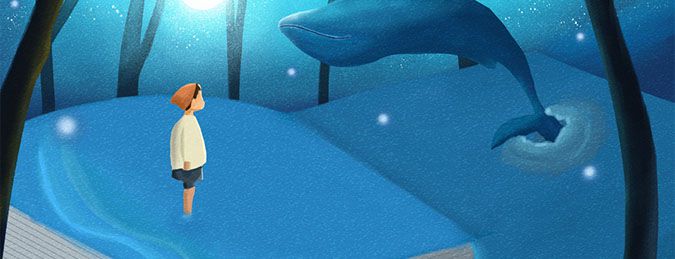最新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必备14篇)。
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 篇1
我对张爱玲的认识并不深,之前对她的文学作品可谓是一无所知,只是潜意识里知道她的文学造诣很高,是位旷世才情的奇女子,仅此而已。
自从进了老年大学,感恩王贤友老师的讲授:《金锁记》里曹七巧心灵变迁历程;《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的人生苍凉、悲壮;以及《旧屋檐下的张爱玲》论张爱玲的价值等等,使我对张爱玲产生兴趣,于是张爱玲不寻常的家庭背景、张爱玲的奇才、张爱玲的贵族、张爱玲的冷傲、张爱玲文字的独特……向我走来,令我目不暇接。
不经意间,我走进了张爱玲的散文《迟暮》,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看她的散文,文章中少年的苍凉,笔力的老道,让我感慨。再看她生平,她写这篇文章时竟然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十二岁小女孩却写出了迟暮美人的心境。更让我刮目相看。
在这篇散文中,张爱玲用她独特的文笔,向人们提醒:青春是宝贵的,更是短暂的。文中描写了一幅在生机勃勃的春天,以及一个迟暮美人对韶光易逝无可奈何的伤感画面……
这个凭栏哀悼的女人正是张爱玲笔下的“封姨”,“封姨”年轻时不仅风华正茂,更拥有华丽的人生。她的容颜与盛气并存,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在民国时期,这种人生,足以令千万人艳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时间的.不断更新,“封姨”青春已逝,面对酒红灯绿的社会,巳赶不上历史的潮流,她觉得自身是时代的落伍者,被时代所抛弃。她已没有资格与春天共舞,所能拥有是内心的空虚、惆怅与悲哀……
美人迟暮,这种亘古以来以时间切割红颜的永久命题,居然被张爱玲稚嫩的小手描绘得如此细腻、圆润、深邃。让我感受到了张爱玲天才的早慧和张爱玲的文字功力!
而今,我巳是“迟暮”老人,庆幸的是,我们生在好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人的寿命已长了很多。“迟暮”已不可怕,正是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挥霍。“迟暮”已变成我们这般老人的第二个春天,我们可以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任意遨游,吟诗作画、唱歌跳舞……培养各自的兴趣爱好;可以组团旅游,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可以和儿孙共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我们和年轻人比美,与社会同进步,按现在的话说“与时俱进”!再也不用凭栏独吟“黄卷青灯,美人迟暮”。
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 篇2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Micronesian)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
述职报告之家(ys575.com)小编精心推荐:
- 散文作品 | 小学作品小草散文摘抄 | 生活散文作品 | 冰心的作品春水的摘抄 | 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 | 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 篇3
无论是“镜花水月的女人”,抑或“才女”,这些称谓都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女”字。我不是在这儿废话连篇地说笑,而是因为张爱玲所表现出的典型而又独特的女性气质,着实让人感慨万千。典型,在于她细心、敏感的女性心理;独特,是因为上下几千年中国女人缜密繁复的心思只有在张爱玲的幽幽叙述中展露无余。
没有丁玲辛辣鞭挞的畅快,亦没有冰心古道热肠的光明,张爱玲散文起初给我的印象是幽绵、晦暗,然而又有无穷无尽值得玩味、思考的意味。她的笔墨并不多姿多彩,却又不乏意象万千、活泼多情的修辞,恰如其分地兼具着古韵之风和诗的烂漫;语言的超常组合更令人拍案叫绝,如:“噎住了阳光”(指黑影),“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指打仗经历),“简单的心”(指夜营的喇叭声)。纵观她的散文,始终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冷色调绵绵流淌于字里行间。换言之,一股淡淡的苍凉总是透过纸张袭上读者的心头。文章是作家的肺腑之言,作品是作家的心境。于是我不得不联想到张爱玲本人的善感、多虑。散文集的编者介绍张爱玲出生于曾经声势显赫的书香门第,家庭的衰败对她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曹雪芹写出举世瞩目的大悲剧,而张爱玲同样也以淡淡的悲融入自己的写作中。于是透过打着烙印的心去观察那个时代的世态人情,一切在她的笔端另生一番情景。用不咸不淡的话娓娓述说暴虐的父亲、无情的姨妈,没有抱怨之言,没有痛恨之辞,却悲从中来;战争中的非凡经历没有使张爱玲刻意去描写绝望和苦楚,而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凉凉地讲述着战争中的人们,略带诙谐的'笔墨中自有不胜的荒凉和凄惨;即使在一些艺术鉴赏文中,她也是以漫不经心的凉凉的语气否定了许多艺术作品,并我行我素地崇尚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
我不同意称张爱玲是无病呻吟的文人。她的散文语意虽淡薄,主题虽谈不上积极,然而她从来没有虚伪地矫饰自己,而是真实地展示着自我。她欣赏日本文化,于是就写了。从这一点上说,张爱玲是坦率透明的。也许我们都误会她了。也许淡雅清冷的隽语正是表达她内心强烈感受的通途。而别人对她的误解正因为她太与众不同了。就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既可看作眷侣之间缠绵悱恻悲悲凄凄的情意,也可以理解成舍己奉献无怨无悔的荡气回肠的倾吐。张爱玲,难道你真是个“情到深处情转薄”的谜一样的女人吗?
-
推荐阅读:
写橘子的优秀散文作品摘抄
小学作品小草散文摘抄(汇总7篇)
感人抒情短篇散文作品摘抄(收藏四篇)
感人抒情短篇散文作品摘抄(合集十一篇)
最新司马迁的作品摘抄(精品4篇)
冰心的作品春水的摘抄(汇总五篇)
-
需要更多的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网内容,请访问至: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作品摘抄